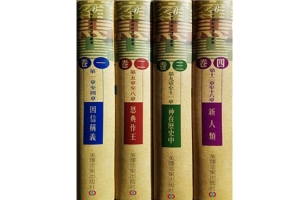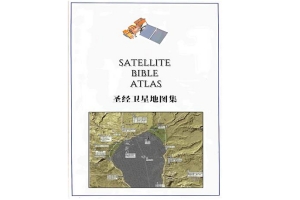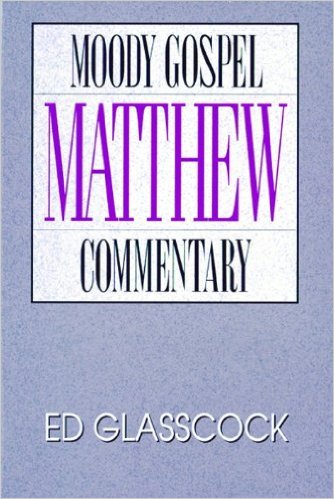宣教士、新教会和长老
20世纪末,东非的卢旺达被誉为非洲大陆福音最广传和最基督教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受洗的基督徒,大部分基督教影响源自于东非复兴。它1927年始于卢旺达,然后传播到不同宗派和附近国家。[1]
然而在1994年,人口占少数的图西族和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之间发生冲突,前者被后者驱逐,但后来尝试重新控制政府。最终,这场冲突导致在这个人口不到900万的国家里,将近100万人遭受屠杀。在一次宣教会议上,詹姆斯·恩格尔(James Engel)的这番话表达了卢旺达一些国民的感受:“你们有传福音的全部热诚,把基督带给我们,但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如何生活。”[2]卢旺达福音神学院的一位毕业生解释了卢旺达教会的标准做法:“我们使用圣经,但我们其实并不按圣经思考,也不总是能准确地教导圣经。”[3]约翰·罗伯(John Robb)和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观察到,由于教会未能“对百姓进行门训”,卢旺达教会里大多数人成了挂名的基督徒。[4]前往卢旺达宣教的第三代宣教士梅格·吉尔博(Meg Guillebaud)亲眼见证了领袖的不敬虔以及肤浅的教导,“结果是基督徒没有受到门训”。[5]她进一步指出一种普遍的宗教融合主义,这削弱了基督教在这个福音广传之国的影响。[6]虽然卢旺达曾经被誉为福音的好土,但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却摧毁了国民对教会的信心,因为有许多认信的基督徒参与了杀戮。[7]
如果卢旺达教会的领袖按着耶稣的命令,把神的话语忠心地教导给人,并用真道门训他们,使教会学会按圣经思考问题,那么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人们像重视大使命的第一条嘱咐(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那样重视最后一条嘱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卢旺达教会的快速增长所留下的领袖缺口本可以被填补。大使命要求有持续的教导和训练。[8]
在复兴时期,卢旺达享有官方的宗教自由,但这个地球上其他禁止公开传福音,信徒经常面对逼迫的地方,又如何呢?什么能够防止新信徒重回他们从前的信仰,或把迷信与基督教敬拜融合起来?在这世界上的“艰难地区”,即教会迅速发展和受逼迫的地方,宣教士所面临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识别和培养领袖。虽然在教会泛滥的地方,植堂者们也面对同样的需要,但在几乎没有成熟基督徒的地方,问题就大不相同了。[9]使人作主门徒的愿望也必须包括教导和训练他们。本章的论点就是,在艰难地区新的教会必须识别和培养教牧领袖(长老),这些人将教导、示范、训练教会,让教会走向灵命的成熟。在植堂运动(Church Planting Movements,CPMs)中留下的许多没有领袖的教会,以及在逼迫使得培养领袖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发展领袖就特别具有挑战性。我们在这一章要探讨宣教士为什么必须以及如何把发展领袖和在新的教会设立长老当作优先要务。此外,我要根据教牧书信查考一个人信主后多久可以担任长老,最后提出在艰难地区发展领袖的计划。
宣教的困境
宣教学教授布鲁斯·阿什福德指出,美南浸信会信徒“长久以来一直为在世界上甚至我们自己国家的未得之民当中兴起植堂运动祷告和努力”。[10]一些被报道出来的植堂运动出现在众所周知的基督徒遭迫害的地区。但他正确地警告说,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加增神的荣耀和国度”,那么就不应该用任何东西,尤其是违背圣经的简化方法取代神的荣耀的优先地位。“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仅关注速度,也要关注福音的纯正和教会的健康。”因此,“过分强调速度”,或只强调教义纯正却不关注增长,都是不可取的。[11]
然而,如果神乐意让教会快速增长,有点讽刺的是,这样的好消息可能反而会让植堂者和宣教士感到为难。快速增长的教会需要快速成熟的领袖来牧养,因此宣教士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有领袖潜质的信徒多快可以被认可作长老。[12]一个人的年龄和信主时间是否应当成为任命领袖的考虑因素?在容易遭受逼迫的地方,教会只有刚刚信主的人,那么应当如何努力迈向成熟?
在逼迫普遍的地方,这问题就更突出。一位宣教士可能需要限制他与新教会在一起的时间,免得他的出现危及他们。然而未能在新诞生的教会中确立某种形式的带领,这就是严重的失职。宣教学家大卫·西尔斯(David Sills)提醒我们:“启创式国家(creative access country,译者注:因为不允许公开宣教,使得宣教士必须使用有创意的方式才得以进入和居留的国家)的挑战,并不意味着人们无需遵守圣经的命令。但凡基督命令的,都要教训人遵守。”[13]宣教士必须制定合适的计划牧养新教会,即使这牧养似乎并不足够。具体来说,他面对三重挑战:(1)认真训练和设立那些具备提摩太前书第3章和提多书第1章所要求的品格的领袖;(2)快速建立一个比宣教士本人在他们当中的事工更长久的带领架构;(3)把教会交给能保护他们的主。这是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行期间遵循的模式(徒14:23)。宣教领袖丹尼尔·辛克莱(Daniel Sinclair)把这称为使徒及同工们在植堂时“一贯的目标”。[14]他们努力建立一个领导团队来牧养新建立的教会。
每一间地方教会都需要本土领袖,在大多数教会中“这应该由多位长老组成”。[15]这是每一间教会都应当追求的理想。然而,环境的不同需要人在圣经范围之内发挥创意,建立一种初步的带领框架,以满足需要,直到达成理想。宣教士要防止把西方教会的模式硬搬到植堂运动或受逼迫的环境中。正如爱德华·戴顿(Edward Dayton)和大卫·弗雷泽(David Fraser)正确指出的那样,宣教士“必须让教会的真本质,而非组织、机构和传统等次要特征发挥主导作用”,分清楚“圣经中的范例和命令之间的不同”。[16]在为新教会打下继续教导和带领的基础时,必须把圣经放在中心地位。即使在宣教士处境化地考虑问题时,这依然至关重要。
教会的必需:确认教牧领袖的原因
新约圣经要求教会有合乎资格的领袖,以此维持地方教会的健康。[17]这确实是一间健康教会必不可少的标志。[18]无论称为长老、牧师还是监督,领袖都必须重视教导、示范、训练、劝勉、管教和纠正的工作。19世纪的一位长老会信徒大卫·迪克森(David Dickson)解释说:“某种形式之下的长老带领,对于一间健康和为神所用的教会来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19]他继续说明不同类型的教会如何采用某种形式的长老制(循道会采用的是等级领袖,浸信会和会众制教会是执事,主教制教会是一种正式认可的平信徒组织)。[20]换言之,领袖的名称或头衔不及其品格和作用重要。菲利普•莱肯既是牧师,又是一位神学家,他认为长老带领对于保护神对教会的投入来说至关重要。他断言:“神的计划是把教会置于牧者看顾之下。”[21]丹尼尔·辛克莱同意这说法,指出按照他对拓荒式宣教工作的全面观察,未能建立众长老制的教会不可避免地会分崩离析,而实行众长老制的教会则会兴旺。[22]因此,对于宣教士和植堂者来说,设立教牧领袖这一目标绝非可有可无的事。
有一个原因是相当明显的:教会成员是羊,需要牧者引导他们走向灵命的成熟。他们不该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太9:36)。保罗和彼得跟从主的带领(徒20:28;彼前5:2;参见约21:16),都使用“牧养”(poimainein)这一动词描述看顾、保护和培育的工作。[23]
在总体上,新约圣经中的使徒和长老为发展健康教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样式,比如保罗的例子,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西1:28-29)。“我们传扬他”这句话中的“我们”是复数,这就是说,传福音和造就门徒的工作是属于更广泛的教会的工作,而不仅仅是使徒的工作。[24]将来一代又一代的教牧领袖也要承担同样的责任。我们从经文看到的责任包括“劝戒各人、教导各人”。看来传扬基督要求教牧领袖参与积极的牧养和持续的教导。[25]奥布赖恩(Peter O’Brien)说:“除非每一位信徒都达到完全成熟,不然保罗作为一位真正的牧师,就不会满足”[26]每一位教牧领袖必须要有相同的目标。
基督徒会走偏路而陷入犯罪、虚假的教导、异端、不合一、甚至宗教融合主义,这就要求教牧领袖保持警惕和采取恰当的纠正措施。[27]西尔斯讲到他在安第斯地区本土牧师当中工作时观察到的宗教融合主义,包括把他们喝剩的残渣浇奠给一位土地女神,以及在一个小孩子的葬礼中融合了天主教、精灵崇拜和福音派传统。[28]如果没有敬虔、受过训练的领袖,教会无法保护自己。
教会带领和教会的成熟
每一间教会要成长,都需要定期地在圣经方面接受训练。这就需要教会有不断成熟的领袖,用神的话语持续地教导和训练他们。[29]巴刻把对圣经的认识置于在敬虔上长进的核心地位,指出真正的敬虔在于以下三个方面:“(1)相信神的应许的生活……(2)这包括顺服神的律法……(3)总有以神的真理为乐作为标记。”[30]若不认识圣经,一位认信的信徒就没有能力在敬虔中长进。
这意味着传福音和持续教导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工作”,仿佛互不依存。[31]相反,训练刚信主的人在敬虔中长进,既保护福音的纯正,也带来吸引人的传福音的见证。所以那处伟大的传福音经文(即大使命)预见到教牧领袖忠心教导神的群羊遵守基督的命令是必要的(太28:20;也见彼前5:1-5),这就不足为奇了。
保持福音的纯正与在敬虔中长进是相辅相成的。保罗责备加拉太人,因为他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加1:6)。虽然教会应当集体参与,但是作为教会的柱石和根基(提前3:15),长老应当站在前线保守福音。保罗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分享这种担忧,警告他们“豺狼神学”要渗透进来扭曲基督教信仰。他也指示提多把在克里特岛众教会中设立长老当作优先要务。长老要努力防备一些人,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多1:11)。斯托得很好地概括了新约圣经的防卫策略:“假师傅增加的时候,最恰当的长期策略就是增加真教师的人数,这些人得到装备,可以批判和驳斥错谬。”[32]在快速增长的教会中,刚信主的人需要教牧领袖的指引和教义训练,不然,这些人就很可能落入虚假的教导。[33]
作群羊的榜样
在艰难地区新建立的教会不仅需要教义上的保护,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看到的,他们也需要基督徒生活的好榜样,真实地展现如何按福音的要求生活。约翰·哈米特把这个包括在教会牧者的四种责任之内:(1)神话语的事工;(2)教牧事工;(3)进行照管或带领;(4)作群羊的榜样。[34]领袖很有可能在教导和照管方面做得很好,然而却忽视了作为牧养领袖对基督徒生活的亲身示范。
保罗告诉他派到以弗所教会的代表提摩太,总要……作信徒的榜样。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提前4:12,16)。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那时提摩太已经效法他的榜样: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提后3:10,11)。保罗劝勉腓立比人: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腓3:17)。[35]只有教义还不够,教牧领袖也必须表明基督徒生活如何触及关系、群体、家庭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领袖:总是当务之急
在美国教会迅速扩张时,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美国教会与全世界其他地方都迫切地需要属灵带领。然而主要的区别在于,北美的教会有更多的属灵领袖人选,有近乎无穷多的资源用来帮助新教会,直到教会内部兴起领袖。[36]
然而在第三世界情况并非如此,大多数教会领袖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宣教教育者小约翰·巴尔默(John Balmer, Jr.)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事实上,在第三世界大概有200万教牧领袖,他们当中的180万人(百分之九十)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牧培训。”[37]缺乏神学教育常常带来宗教融合主义,就好像精灵崇拜依然在扭曲的、次基督教的框架中延续。[38]解决之道并不一定是要建立西式的神学院。成本、政治法规和其他后勤因素可能让这种做法不切实际。而且,民族优越感让西方人忽略了把神学培训处境化地带给一个特定人群。[39]神学家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解释说,对某种形式和释经方法的倾向会导致宣教士很自然地对第三世界国家人们的神学思考“施加强大的影响力”,而不是帮助他们直接用圣经世界观考虑问题。[40]因此,训练教牧领袖的办法,并不是把西方的架构搬到第三世界国家。相反,在新教会的文化处境当中,宣教士需要在内容上加强,而在形式上灵活。[41]
没有神学院训练的领袖
在福音工作几乎还没有展开的地方,对教牧领袖有一种特别的需求。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人们对圣经的认识很少,宗教融合主义和虚假教导的问题严重。美国基督徒可能注意到,他们的国家里有大量接受过神学院训练的人没有在教会里供职,于是就认为在全球都人才过剩。但情况并非如此。学园传道会的史蒂夫·克林顿(Steve Clinton)进行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察:虽然全世界的神学院毕业生人数在上升,却完全不能满足全球的需要。即使毕业生的人数在接下来40年时间里稳定保持在每年15000名,但也只有60万新的毕业生。“然而,如果教会增长速度保持稳定,我们在接下来40年就需要500万名新牧师。那么,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的新兴教会,其教牧领袖没有接受过神学训练。”[42]当然,神学院训练并不是主要目标,但这数据确实反映出需要。
初期教会坚固他们工作的成果。使徒以多重方式确保教会在信心上成熟。学者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解释说:“使徒回访他们带领信主的人,设立长老看顾他们,给他们写信,派使者到他们那里去,并为这些人祷告。”[43]这是现代宣教植堂者应当遵循的模式:继续探访,培训领袖,保持联系,派出信使和祷告。建立类似的模式使得宣教士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继续教导,直到他有了“受过训练的训练者”来延续有效的教牧带领。[44]
如果宣教士和植堂者在艰难地区的教会训练那些将来的训练者,那么神学院的培训虽然有优势,也并非必不可少。通过前者,领袖们可以逐渐学习纯正的教义、教牧技巧和处境化的教会论。宣教学家吉姆·斯莱克(Jim Slack)说,在一批接受调查的由植堂运动建立起的教会中,几乎没有受过神学院训练的领袖。相反,领袖是在教会或在群体之内兴起的。“在每一个接受评估的植堂运动建立起的教会中,他们的教牧领袖都是从本地兴起的平信徒领袖。其中只有一间教会有几个受过神学训练的全职牧师……大多数教牧领袖都是从新教会内部涌现出来的。”[45]这似乎与从新约圣经中观察到的模式一样(徒6:1-7,14:21-23;多1:5)。
教会必须接受训练,以服侍基督的身体和不信的世人(弗4:11-16)。格林强调了以合乎圣经的方法来装备一间教会进行全方面的基督教事工:“神首要的方法是人,重生的、分别为圣的、委身的、有动力的、受过训练和装备的人。神首要的器皿是教会,教会是委身之人的群体。属灵领袖和一群有动力的、受过训练的教会成员是神对推进他事工提出的要求。”[46]教会的扩展是培训的主要目标。教会对其成员的训练和动员程度如何,决定了教会传福音的有效程度如何,而这主要是通过有效的教牧领袖来实现的。[47]
首要的事情
无论在植堂运动还是在逼迫的处境中,宣教士植堂者都需要立即为新的教会评估潜在的领袖。要这样做,他应当咨询那些熟悉当地文化的人,他们了解潜在领袖在群体中的名声如何。那些对。[48]当然,培训领袖会让他放慢建立下一间新教会的脚步,但基督在大使命的最后一个要求预见到教会需要训练领袖,后者能够定期装备新的教会。正如拓荒宣教学家罗兰·艾伦(Rolland Allen)指出的那样,这是使徒保罗的做法:在一个地方讲道五到六个月时间,然后离去,留下一间建立起来的有长老带领的教会。保罗把精力集中在本土化上,而不是留下一间要依赖他的教会。[49]他回访之前建立的教会,证明了这些教会的存在已经不需要使徒的严密监管。他训练领袖认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使他们能将这些事传递给其他人(提后2:2)。[50]
什么是训练?科林·马歇尔(Colin Marshall)和托尼·佩恩(Tony Payne)很有智慧地解释说:“在新约圣经中,训练更多的是关于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而非具体的技巧或能力。”[51]因此,宣教士可能没有机会、甚至不需要模仿他曾接受过的学术训练。他的关注点必须是培养那些知道如何按圣经思考问题,并把圣经应用在生命当中的教牧领袖。“训练的核心并不在于传递一种技能,而是传递纯正的教义。”[52]这与西方的一些方法相反。“保罗使用‘训练’的说法来指向一个毕生的过程:提摩太和他的会众在圣经的教导下拒绝假宗教,并在他们的内心和生命中都遵从纯正的教义。好的圣经训练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建立在纯正的、使人灵命健康的教导之上的敬虔生活。”[53]宣教士不能简单地给潜在的领袖一本关于作长老的手册,盼望会有最好的结果。训练是“深入的,并且不可避免地是关系性的”。[54]你只需要看一看保罗与提摩太、提多的关系,就能明白关系的必要性。“这种亲密的关系是一个载体,传递了保罗训练提摩太的一种关键元素,就是效法。”[55]保罗实质上是在传递一种生命之道,受训的人只有看着这位使徒示范才能明白。[56]现代的宣教士必须遵循同样的模式。
教会往往反映其领袖的样子。如果领袖未能把纯正的教义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教会有可能就会步其后尘。虽然领袖可能相对来说是新信徒,但如果他善于从与宣教士的关系中学习,他就能大大地帮助其他人在新的教会中看到福音是如何应用在生命当中的。“训练的关系型本质意味着最好的训练经常是通过耳濡目染,而不是正式的教导发生的。这既是接受教导,也是亲身领会。接受训练的人最终会与训练他们的人很相像,正如孩子长大像父母一样。”[57]马歇尔和佩恩把训练的性质和目标归纳为三个焦点:“信念,即他们对神的认识和对圣经的理解;品格,即与纯正教义相符的敬虔品格和生活;能力,即有能力带着祷告的心,以不同的方式对其他人讲述神的话语。”[58]一位训练潜在领袖的宣教士,可能喜欢对将来的教牧领袖讲论教会历史、系统神学和护教学。虽然这看起来很理想,但他可能因着时间和环境的限制,不能提供这种广泛的培训。他需要把信念、品格和能力放在优先位置上。或者,要调整为神学教授兼牧师卫天牧(Timothy Witmer)所说的“有效牧养事工的核心元素”,一位艰难地区的宣教士应当强调那些有关合乎圣经、讲求关系、彼此监督和常常祷告的基本点。[59]他要向潜在的领袖教导圣经,要亲身示范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要展示出彼此监督的必要性,还要通过命令和实践让人看到祷告在牧养事工中的核心作用。
发掘潜在的领袖
宣教士应当如何发掘潜在的教牧领袖?他必须留意那些愿意承担责任、爱群羊、表现出一定的教导能力和忠心的人。这必然要求在新的教会投入时间,询问与潜在领袖有关的问题,并培养那些潜在领袖。艰难地区要求人关注最低要求,而不是理想状态;关注品质,而不是一份资格清单。[60]宣教士与其把将来的领袖与自己认识的成熟教会中更成熟的领袖作比较,不如留意一些表明他们在基督徒行事为人和实践方面有所长进的品质。[61]
如果一位潜在的领袖是刚信主的人,那怎么办?一位宣教士需要投入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位新信徒放在领袖的位置上?艰难地区迫切地需要领袖,这就需要采用与西方常用方法不一样的方式,一种加速确立长老的方式。新约圣经讲到许多在艰难的地区建立教会的情况。因为保罗与大多数教会在一起的时间不到六个月,却将长老分别出来在这些教会当中服侍(例如徒14:21-23),艾伦就得出结论说,这样的时间框架足以确立长老带领。他承认,如果今天有人提议做同样的事,“这人可能被看作鲁莽而近乎疯狂。然而没有人否认圣徒保罗就是这样做的。”[62]艾伦进一步解释说,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新信主的人在认识福音或基督教信仰方面并没有特别的优势。虽然一些人可能熟悉犹太人的律法或希腊哲学,“绝大多数人曾经深陷偶像崇拜的愚昧和罪恶当中,被最赤裸裸的迷信所辖制。没有人在过去对救主的生平和教导有任何了解。”[63]既然保罗能在短时间内,在他建立的新教会中,确定有效的带领架构,今天的宣教士当然也能这样做。那么,现代的宣教士如何平衡对领袖的迫切需求和圣经对教牧领袖的的资格要求?查考教牧书信会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从教牧书信得到的观察
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早期在以弗所建立教会,用了三年时间讲道、教导和门训(徒18:22-23,19:1-10,20:31)。教会确立了长老带领,这一点在保罗踏上去耶路撒冷的生死之旅之前,在米利都与以弗所教会长老见面时得到了证实(徒20:17-38)。他在耶路撒冷被捕,最终被带到罗马,在凯撒面前申诉(徒21:27-40,25:10-12,28:11- 31)。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导致他从公元60年到62年第一次在罗马被囚。在这之后,他被释放了有大约两年时间,而且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中,他做了更多侍奉工作。[64]在这段时间,他似乎与提多到访克里特岛,并把提多留在那里把事情办理整齐,自己则有可能前往了西班牙。[65]保罗在这岛上待了不到一年时间,却足以建立许多教会(多1:5,在各城设立长老)。[66]讲到“在刚成立的教会确立长老,多快才算太快”这个问题,孟恩思对保罗在克里特岛的宣教做了几个观察。[67]他把他的观察建立在内部证据上,就是克里特岛的教会相对较新,这意味着他们们潜在的长老是初信之人。以下是我自己对其要点的解释:
保罗指示提多设立长老,但没有提到执事(多1:5),这表明在教会开始成长之后执事才出现(徒6:1-6)。
保罗并没有像对在以弗所的提摩太所说的那样(提前5:19-21),让提多把犯罪的监督开除,只是说要设立监督(多1:5)。这似乎表明监督在这之前并不存在,因此无需做出纠正。
保罗并没有重复这条命令,即监督不能是初入教的人(参见提前3:6)。这表明要么没有新信之人,要么都是新信之人——前者是不大可能的事,按内部证据来看,后者似乎更有可能。
书信的大部分内容是适合新信徒的基本教理问答,从中带出两个关于救恩的说法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多2:11-14,3:3-8)。这似乎表明教会是新建立的,并且信徒还不够成熟。
假教师的教导虽然成功(多1:11),但影响并不像在提摩太前书中所说的那样大,表明问题并不是非常严重。[68]
另外,新约圣经学者本杰明·默克尔强调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中两份品格清单的显著不同:“提多书省略了不可初入教这一资格。”[69]为什么会有这省略?“这省略可能是因着克里特岛教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而作出的必要修正。在新建的教会中,在信仰上相对年轻的信徒可能需要担任领袖。”[70]正如汤姆斯·利(Thomas Lea)和小海恩·格里芬(Hayne Griffin Jr.)观察的那样,这一修正连同提摩太前书列出的其他品质,可能表明保罗“按地方处境的要求,在教会组织的某些事情上”采取的灵活做法。[71]然而保罗在克里特岛的停留,加上他离岛和写信给提多之间的几个月,给了这位使徒的代理——提多充足的时间来评估合乎资格的长老候选人,并预备他们在克里特岛教会接受按立。[72]保罗打算在冬天之前与提多在尼哥波立会合,因此他期望他的指示快快得以实施(多3:12)。
提多设立作长老的人入教有多久?人们可能会猜测:(1)他们确实是“长老”,也就是说,他们在基督教群体当中是较为年长的人;(2)他们熟稔旧约圣经,因为岛上可能有大批的犹太人群体;(3)他们是30年前在五旬节期间信主的那批人,回到克里特岛建立了类似的基督徒群体(徒2:11)。但这些都是猜测。圣经内在的证据,特别是提多书2:1-8,表明克里特岛的众教会是新近建立的,而且成员的年龄各异。[73]
提摩太和提多有可能并不是他们各自所在教会的长老,而是作为使徒临时的代理或宣教士在教会里服侍。[74]提摩太的事工已经变得比提多的事工更复杂。他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提前1:3-4)。他也有责任传递保罗给教会的教牧指示(提前4:6、16)。赋予他的权柄包括公开责备落入罪中不悔改的长老,以及按立人担任牧师职分(提前5:17-22)。
同样,保罗已经委托提多把自己在教会还没有做完的事办理整齐,在每一座城设立长老,就如之前(应该是他们在克里特岛同工的时候)指示他的那样(多1:5)。提多和提摩太在行使权柄时,是否把会众完全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提摩太和提多可能都让会众参与了他们任命长老的决定,因为正如斯托得观察的那样:“他强调他们要有无可责备的名声,这表明会众在选举过程中拥有发言权。”[75]这与我们之前思考使徒行传的经文时观察到的模式是一样的。
更广泛地说,教牧书信表明了新约圣经对地方教会领袖的教导的一些基本模式。[76]第一,长老应当从教会内部选出,这些人是因着他们的忠心、好品行和参与教会事工而广为人知。第二,应当认真地选举长老。提摩太前书3:1-7和提多书1:6-9指出的具体特征缩小了长老候选人的范围。这两封书信都讲到的重要品格有:无可指责,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家庭,儿女是相信(或忠心)的,有节制,乐意接待人,不醉酒,不打人,善于用纯正的教义教导人和劝勉人,不贪财。[77]而且正如我已经说明的那样,保罗并没有指示提多将刚信主的基督徒排除在长老候选人之外,这表明“不同的教会处境要求教会组织所具有的灵活性”。[78]第三,教牧领袖应当“由多位组成”(就是说,领导层不是被一个人控制)”,[79]很明显,这些教会中并不存在君主式主教治理的概念,这是在圣经成书之后才出现的事。[80]
这种模式在快速发展和逼迫处境中的新教会继续适用。宣教士应当在新教会内部留意潜在的长老,看重教牧书信列出的圣经资格(特别是提多书,因为这些品格看起来更像是为较新的教会制定的),除非只有一个人符合资格,否则总要努力建立多位长老带领。[81]
制定带领计划
在植堂运动和逼迫环境下,宣教士遵循一个连贯的计划,将有助于保存造就门徒的成果。教会必须要有教牧领袖。在一些处境中,因为一个教牧领袖也没有,宣教士会面对艰难的决定,即推荐一些在信仰方面尚年轻的人作长老。他如何确信自己这样做是在跟从主的带领呢?为了帮助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我们确定了在建立地方教会带领过程中的十个焦点。
第一,关注潜在领袖的品格。虽然保罗和巴拿巴在加拉太地区设立长老时(徒14:23),并没有指出提摩太前书第3章和提多书第1章所要求的行为品质,但是吩咐提摩太和提多的细节让我们确信绝不可忽视品格。因为宣教士不大可能找到许多非常成熟的基督徒,他就必须考虑到在他观察这些潜在领袖期间,他们的品格有何发展。具体来说,他应当留意这些人是否有忠心、愿意摆上、为人正直、受教,要特别强调最后一个品质。[82]
第二,因为提多书聚焦在较新的教会,宣教士识别潜在长老时就应当特别留意提多书1:6-9描述的品格特征。理想的情况就是一位候选人具备提摩太前书第3章和提多书第1章列举的所有品质。但考虑到初信主的人、新的教会和艰难地区,人就必须面对现实。狄克逊也提供了有益的评论:
这职分和工作是属灵的,那么长老必然就应该是属灵的人。他们并不一定要有极大的恩赐,或在世上有很高的地位,或有财富,或高学历,但必不可少的是,他们必须是属神的人,与神相和,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要参与到使人与神和好的使命当中,他们自己就必须与神和好。[83]
考虑长老人选时,以下四个问题有效地概括了保罗在提多书第1章提出的要求:
1.他是否是一个忠诚的、注重家庭的人,委身妻子,好好管理儿女(1:6)?[84]
2.他在自己的情感、欲望和关系上是否有节制(1:7)?
3.他能否与他人和睦相处,在待人接物中活出福音(1:8)?[85]
4.他能否正确地使用圣经劝勉和纠正其他人(1:9)?
第三,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两三个人,他们的品格和服侍受到教会认可,配得行使权柄,即带领、牧养、责备、培训、教导和治理的权柄。与会众的尊重程度相比,年纪并不是一个问题。[86]正如雷·斯特德曼(Ray Stedman,又译“司德曼”)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尊重应当“产生于他们(长老们)自己的爱心和敬虔的榜样”。[87]
第四,如果只有一个人符合资格带领教会,会众可以将他分别出来,计划好只要他们能找到另一个人,就马上加进来。在受逼迫的地方,少数几个家庭和个人在小型的家庭教会里聚会,可能更难找到多位长老。但当众长老制正确发挥作用时,它有助于防止专权和独裁。还可以增加侍奉的恩赐,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体系来满足事工需要,让侍奉有更大的果效。[88]
第五,如果只有一个人合乎资格服侍,这位单独的长老可能要有监督他的伙伴或团队来协助他。这些监督他的人并不分享这个权柄,但他们能帮助这位长老留心他的行事为人和教训。[89]
第六,宣教士应当把大量时间投入到潜在长老身上,观察他们如何回应教导,注意他们是否谦卑、他们的个人成长、在神的道和祷告方面的操练、对家庭的忠心,以及在社区中的名声。西尔斯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宣教工具:以身作则、协助、观察和离开(MAWL)。“这要求学徒观察师傅,然后操练……当学徒‘独当一面’而不出差错时,师傅就可以离开了。”[90]辛克莱认为这过程要用两到六个月时间,着重关注“集中性的品格操练”。[91]宣教士用这种方法能密切留意潜在的领袖如何成长,然后才把他们交给新的教会。
第七,植堂者不应当试图强制要求潜在的教牧领袖接受西式的神学院教育,而是要提供一些侍奉训练的核心内容。[92]艾伦探索了这问题:“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他(保罗)如何训练他引导归主的人,以至于可以在如此短时间内离开他们,相信他们能站立得住并继续成长。”[93]那么,要考虑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以下是七种可能:
1.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点,强调合乎圣经的神学。教导他们福音。[94]
2.简单的释经原则。
3.属灵操练的模式。[95]
4.在个人行事为人和顺服方面彼此监督。
5.属灵领袖的基本责任:教义、管教、制定方向和在基督徒生活方面以身作则(例如徒20章;彼前5章;多1:5-9)。
6.实行教会纪律——如何实行,何时实行(太18:18-20;林前5章,等等)。
7.对会众进行门训。
第八,宣教士应当为新领袖指出需要教导和服侍教会的领域。吉恩·盖兹指出了六项优先:“教导神的道,示范基督式的行为表现,持守教义的纯正,管教不顺服的信徒,照管教会的物质需要,以及为病人祷告。”[96]这些是在新教会中长老主要的“职责”。
第九,如果宣教士和会众担心刚刚设立的教牧领袖在信仰方面太新,那么可以设立他们作临时长老,直到他们能证明自己为止,听从提摩太前书3:6的警告:“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宣教士霍根(Brian Hogan)建议设立“临时长老”或“见习长老”,这些人可以服侍到有更成熟的人可以合格地带领教会为止。[97]
第十,在充分的培训和观察之后,会众应当把这些人分别出来,作会众的牧者或长老,而宣教士则按照保罗在使徒行传14:23-24和20:31-32中的榜样,把他们交托给主。
结论
即使在植堂运动和逼迫环境中,训练领袖也必须是宣教士的优先要务。否则,尽管人们在传福音上热心地努力,大使命却仍然无法实现。要记住,卢旺达教会的失败在于他们未能培养忠心的教牧领袖来教导百姓。宣教士/植堂者绝不可为了接触最多的人而忽略基督的命令,就像在卢旺达所发生的那样。新约圣经决不支持为了追求更多的人数,而忽略了基督吩咐他的门徒所教导的一切。真门徒努力顺服耶稣基督为主,即使在艰难地区也是如此。
很明显,教导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正如宣教学家赵天恩(Jonathan Chao)所强调的那样,宣教士“必须承认基督在他所有的教会之上作王掌权”。[98]在打下合乎圣经的根基之后,他必须把教会的治理交托给本地长老,由他们来承担教导、带领和牧养的责任。虽然他可能纠结于要在新的教会确立完全成熟的领袖的理想化愿望,他却很可能需要采取保罗对克里特岛教会的一些灵活做法。他设立的一些长老可能看起来在信仰方面“太新”,但在这方面他需要有极大的分辨力和圣灵的引导。罗兰·艾伦很有智慧地指出,既然保罗能在一座城停留六个月时间,建立一间教会,并把长老分别出来,将他们交给主,那么现代的宣教士也同样可以这么做。[99]虽然无人能提出一个强制的年龄或信主时间作为担任长老的先决条件,但宣教士需要谨慎地考虑属灵领袖所需的基本素质,然后前进,将教会交给主看顾。与新领袖和教会保持关系,不是从外部施行控制,而是作为一位属灵的父亲提出忠告和鼓励,就像保罗回访他建立的教会一样,这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有智慧的做法。
[1] Patrick Johnstone, Operation World: The Day-by-Day Guide to Praying for the Worl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3), 472 ; Glenn Kendall, “Rwanda,”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Missions, A. Scott Moreau,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0), 842-843.
[2] James Engel, “Beyond the Numbers Game,”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7, 2000, 54 in David Sills, Reaching and Teaching: A Call to Great Commission Obedience (Chicago: Moody Press, 2010), 55.
[3] Alexis Nemeyimana, African lnland Mission On-Field Media. So We Do Not Lose Heart, video from AIM International Online, MPEG; accessed September 20,2009; in Sills, Reaching and Teaching, 162; italics Sills; http://www.aimint.org/usa/videos/so_we_do_not_lose_heart.html.
[4] John Robb and James, The Peace-Making Power of Prayer: Equipping Christians to Transform the World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00), 178-179.
[5] Meg Guillebaud, Rwanda: The Land God Forgot? Revival, Genocide, and Hope (Grand Rapids: Kregel, 2002), 285.
[6]同上,287页。
[7] Kendall, “Rwanda,” 843.
[8] Sills, Reaching, 55, citing Paul Washer, “Gospel 101,”HeartCry Magazine 54 (Sept-Nov 2007):6.
[9] Bruce Riley Ashford, “A Theologically-Driven Missiology,” in Chuck Lawless and Adam Greenway, eds., Great Commission Resurgence: Fulfilling God’s Mandate in Our Time (Nashville: B & H 2010), 202-203,他指出与植堂运动相关的两个宣教问题。第一个是关于植堂运动神学和方法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本章的焦点,即“一个人信主后多久能被认可担任长老”。这个情况在植堂运动和逼迫的处境中均会出现,因此本章要考虑两种情形中总体的带领需要。
[10]同上,202页。
[11]同上,202-203页。
[12]同上,202-203页。
[13] Sills, Reaching and Teaching, 68.
[14] Daniel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Pioneer Church Planting in Teams (Colorado Springs: Authentic Publishing, 2005), 219.
[15] Gary Corwin, “Church Planting 101,” Evangelical Missions Quarterly (April 2005, 41:2). 142.
[16] Edward R. Dayon and David A. Fraser,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rev.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0), 242.
[17]见使徒行传1:15-26,2:42-47,4:32-35,5:1-11,6:1-7,11:19-26,14:21-23,20:17-35;帖撒罗尼迦前书5:12-13;提摩太前书3:1、5,5:17;提摩太后书1:6-8,4:1-5;提多书1:5-9;希伯来书13:7、17;雅各书5:14-15;彼得前书5:1-4的例子。
[18]见狄马可,《健康教会九标志》,rev. ed. (Wheaton, IL: Crossway, 2004), 218-243。
[19] David Dickson, The Elder and His Work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04 from 19th C. reprint, n.d.), 26;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强调不可千篇一律地践行众长老制。
[20]同上。
[21] Philip Graham Ryken, City on a Hill: Reclaiming the Biblical Pattern for the Church in the 21st Century (Chicago: Moody, 2003), 97-98.
[22]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220.
[23] BDAG, 842.
[24] James D. G. Dunn, The Epistles to the Colossians and to Philemon, NIGTC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124.
[25] Peter T O’Brien, Colossian, Philemon, WBC (Waco, TX: Word Books, 1982). 87. See also Eduard Lohse, Colossians and Philemon, Hermeneia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1971), 77.
[26] O'Brien, Colossian, Philemon, 90.
[27]见马太福音18:15-20,这段经文呼吁在教会中采取纠正性的教会纪律措施;也请留意许多关于门徒走偏路,因此需要牧者纠正、警告和教导的例子:哥林多前书3:1-8、16-20,5:1-13;加拉太书1:6-9,3:1-5,5:7-9;腓立比书4:2-3;帖撒罗尼迦前书5:14;帖撒罗尼迦后书3:6-15;提摩太前书1:3-7、18-20,4:11-16;提摩太后书2:22-26,4:10;提多书1:10-16,2:6;希伯来书5:11-14,6:9-12;彼得后书1:8-15;约翰一书5:16、21;约翰二书7-11;约翰三书9-11;启示录第2-3章。
[28] Sills, Reaching, 161.
[29]例如马太福音28:19-20,21:15-17;使徒行传20:28;以弗所书4:11-16,5:19;提摩太前书4:11-16,5:17;提摩太后书2:2、14-15,3:14-17,4:1-5;提多书1:3、9;希伯来书2:1-4;雅各书1:18-25;彼得前书1:22-2:3;彼得后书1:19-21,3:14-18.
[30] J. I. Packer, God Has Spoke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79), 126-132,黑体为原作者所加。
[31] Sills, Reaching, 36.
[32] John Stott, Guard the Truth: The Message of 1 Timothy &Titu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6), 179.
[33]见Witmer, Shepherd Leaders, 45-73,他追溯历史,观察在地方教会中长老带领的兴衰,以及这对教会相应的影响。
[34] John S. Hammett, Biblical Foundations for Baptist Churches: A Contemporary Ecclesiology (Grand Rapids: Kregel Academic & Professional, 2005), 163-166.
[35]保罗使用summimetai(“一同效法的人”)和tupon(“形态、样式、模范、〔道德〕榜样”)这样的词,强调了要为教会树立具体的榜样。BDAG, 958, 1019-1020。
[36]在2009年,有将近7万名学生就读于ATS认证的神学院(ATS即美国与加拿大神学院协会);“Annual Data Table,”2010年9月15日存取,http://www.ats.edu/Resources/ publications/Documents/AnnualDataTables/2009-10AnnualDataTables.pdf.
[37] John Balmer, Jr., “Nonformal Pastoral Ministry Training in the Majority World: Four Case Studies (D. Min. Diss., Columbia Biblical Seminary and School of Missions,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2008), 1, referencing Ramesh Richard, “The Challenge Before Us,” address given at Trainers of Pastors 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TOPIC) Conference, December 1-3,1997. Wheaton, IL (lecture given December 1, 1997); Ralph Winter, “Will We Fail Again?” Mission Frontiers, 1993, 15:7-8; Winter, “Editorial,” 1994, 16:1-2; Winter, The Challenge of Reaching the Unreached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6), n.p.
[38] Sills, Reaching, 161-162.
[39] David K. Clark, To Know and Love God: Method for Theology (Wheaton, IL: Crossway. 2003), 100.
[40] 同上,112-113页。
[41] Sills, Reaching, 168.
[42] Steven Clinton,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ation Factors and Leadership of Spiritual Movements,” EMQ, April 2005, 41:2, 191.
[43] Michael Green, “Methods and Strategy in the Evangelism of the Early Church,” J.D. Douglas, ed,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Lausanne, Switzerland (Minneapolis: World Wide Publications, 1975), 167.
[44] Sills, Reaching, 46.
[45] Jim Slack, “Church Planting Movements: Rationale, Research and Realities of Their Existence,” Journal of Evangelism and Missions, vol. 6, Spring 2007, 41-42.
[46] Green, “Methods and Strategy,” 195.
[47]同上。
[48]与布鲁斯·阿什福德的通信,2010年9月30日。
[49] Roland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2), 83-84.
[50]与艾伦的观点相反,19世纪前往中国的长老会宣教士倪维思(John Nevius),The 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es (Phillipsburg, NJ: P& R, 1958), 27-28,他的意见就是,采取一种更缓慢、更刻意的方式进行培训,若有必要花上数年也可。倪维思也为中国教会制订了一种西方模式,32-44.
[51] 科林·马歇尔和托尼·佩恩,《枝与架:论教会事工与福音成长》(Kingsford, Australia: Matthias Media, 2009), 70.见提摩太前书1:11-12、18-20,4:7,6:11-14、20-21;提摩太后书2:2,3:16、17。
[52]同上,71页。
[53]同上。
[54]同上,71-72页。
[55]同上,72页。
[56]同上。
[57]同上,76页。
[58]同上,78页。
[59] Witmen, The Shepherd Leader, 193-224. 他也补充说,有效的牧养事工应当是系统、全面和实用的。但在艰难地区培训领袖,以上所指出的四点应当成为训练领袖时的优先要务。如果时间和环境许可,还可以扩充,把其他元素包括进来。
[60]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228; Sills, Reaching, 64,他指出最低要求是教导“圣经、纯正的教义,为跟从的人作敬虔生活的榜样”。
[61]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228-231,他补充说:“数个世纪以来,神通过极其有缺陷的植堂者和不完全的地方教会信徒扩展教会的疆界。我们都是残缺的器皿,神是在医治和挽回的过程中动工。这对我是鼓励”(230-231页)。
[62]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85.
[63]同上。
[64] Thomas D. Lea and Hayne R. Griffin, Jr., 1, 2 Timothy, Titus: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Exposition of Holy Scripture (NAC, 34;Nashville: Broadman Press, 1992), 41.
[65] 威廉·孟恩思认为使徒首先到访克里特岛,然后按照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去了西班牙。ln Pastoral Epistles (WBC, 46; Nashville: Nelson. 2000), lix.认为保罗去了西班牙的观点源自于克莱门,他写信说保罗“在东方和西方(讲道)……向全世界教导义,直到西方极尽之处”。1 Clement 5:7; ANF 1:6; A. D. 30-100. Eckhard Schnabel解释说,“直到西方极尽之处”通常被用来代指西班牙。Eckhard J. Schnabel, Paul the Missionary: Realiti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8), 116.引用《克莱门一书》5:6-7,连同《彼得行传》和《穆拉多利正典》(the Muratorian Canon),作为保罗西班牙宣教的进一步证据,117。其他学者指出这缺乏圣经内在的证据,因此不像Schnabel那样肯定保罗确实去了西班牙宣教,见James D. G. Dunn, Romans 9-16 (WBC, 38B; Dallas: Word, 1988), 871-873; Ben Witherington, Paul’s Letter to the Romans: A Socio-Rhetorical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4), 362-363; Douglas J. Moo,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NIC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899-902.
[66]同上,lx. Schnabel, Paul the Missionary,采用的日期稍有不同,认为保罗第一次被囚罗马是在公元60-62年,而在克里特岛稳固新教会大约是在公元63年。
[67] Ashford, “A Theologically-Driven Missiology,” 203.
[68] Mounce, Pastoral Epistles, lix-lx aided by comments from Benjamin L. Merkle, “Ecclesiology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in Andreas Köstenberger and Terry Wilder, eds., Entrusted with the Gospel: Paul’s Theology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Nashville: B & H Academic, 2010), 183-186.
[69] Merkle, “Ecclesiology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185.
[70] 同上。
[71] Lea and Griffin, 1, 2 Timothy, Titus, 278, fn. 11.
[72] Mounce, Pastoral Epistles, lx.
[73]同上,lix-lx.
[74] Merkle, “Ecclesiology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196-198.
[75] Stott, Guard the Truth, 174.
[76] Lea and Griffin, 1, 2 Timothy, Titus, 276-277.
[77] Gene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God’s Plan for Leading the Church: A Bibl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Chicago: Moody, 2003), 157.
[78] Lea and Griffin, 1, 2 Timothy, Titus, 278.
[79]同上。
[80] Merkle, “Ecclesiology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 185.
[81]见对众长老制及其合理性的讨论,W. B. Johnson, “The Gospel Developed through the Government and Order of the Churches of Jesus Christ,” in Mark Dever, ed., Polity: Biblical Arguments on How to Conduct Church Lif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urch Reform, 2001), 192-195.
[82] Lea and Griffin, 1, 2 Timothy, Titus, 279;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235,使用了对人有帮助的缩写说法,“一些人讲到要找那些FAT:faithful(忠心的),available(可用的),teachable(受教的)人。”
[83] Dickson, The Elder, 30.
[84]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163-171.
[85] 关于活出福音,请见J. Mack Stiles, Marks of the Messenger: Knowing, Living and Speaking the Gospel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0), 49-60.
[86]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287-289.
[87] Ray Steadman, Body Life (Glendale, CA: Regal Books, 1972), 82.
[88]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241-242.
[89] 同上,273, 276页。
[90] Sills, Reaching, 49.
[91] Sinclair, A Vision of the Possible, 236.
[92] 见David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5-6,富有洞见地考察了各种西方强加的模式。
[93]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87.
[94] 同上。
[95] Donald S. Whitney, Spiritual Disciplines for the Christian Life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 1991).
[96] Getz, Elders and Leaders, 266.
[97] Brian Hogan, “Distant Thunder: Mongols Follow the Khan of Khans,” in Ralph Winter and Steven Hawthorne,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3rd ed.,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9), 694-695, 696.
[98] Jonathan T’ien-en Chao, “The Nature of the Unity of the Local and Universal Church in Evangelism and Church Growth,” in Douglas, 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1111.
[99] 参见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8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