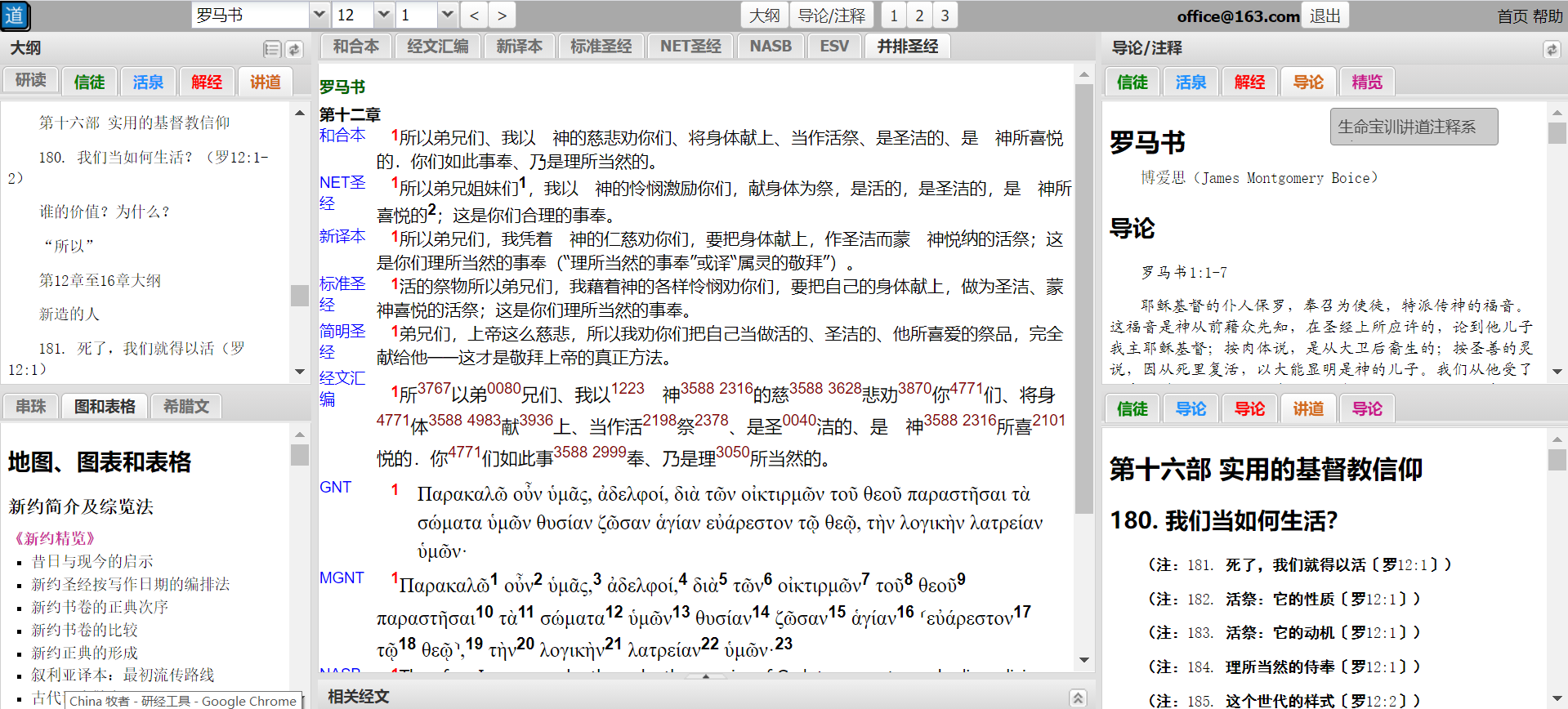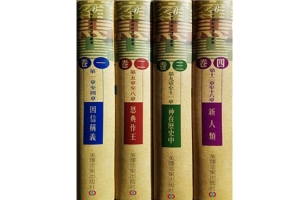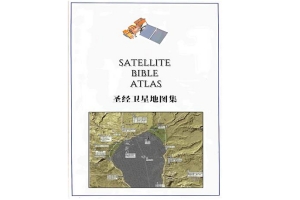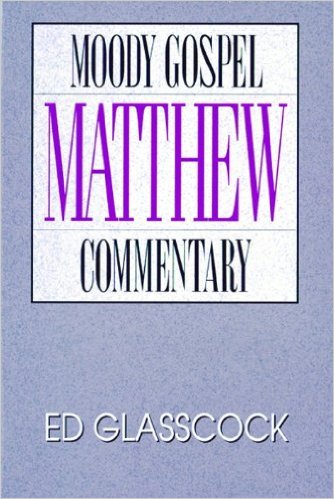罗马书13:3-4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我们正在研究基督教有关政府的教义——当然这是指神所设立的政府——我们面对着现今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权力。每一个人都对权力有兴趣。我们想要有控制自己生活的权力。我们说到有权有势之辈,通往权势之途等等,甚至教会也无法豁免权力斗争。最近有一本书出现,就是与这种可悲的趋势抗衡,其书名是《权能宗教》(Power Religion)。
我们讨论权力,因为它是罗马书第13章提到基督徒必须顺服世俗掌权者的第二个原因。我们在研读第2节时已经讨论了第一个原因:权柄是神建立的,我们若抗拒掌权者,就是抗拒神。我们应当顺服政府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也将审判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若不顺服,就会自找麻烦,因为国家有权力执行其宪法和法律。
保罗这样表达他的观点:“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13:3-4)。在这几节里,保罗用剑来象征政府的权力。
政府的势力
剑的权力就是指势力。这是神赐给国家的,也是政府施政时所凭借的基础。
我们不喜欢思想这方面的事,因为在我们所谓“自由社会”中,强制一个人去做某件事是不对的。就拿养育儿女来说吧!今天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应该强迫孩子做事。我们不可说,“把你的床迭整齐!”或“把饭吃光!”我们乃是提供选择,告诉他们这样做“对你有好处”,或者以奖励代替惩罚。我们说:“你现在要不要吃晚餐(或早餐)?”甚至说:“你喜欢先吃马铃薯或先吃菠菜?”若有人告诉我们“必须”做某件事,即使我们这些成年人都会浑身不自在。
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心态,我们想到政府,特别是一个广孚人望的政府时,就不愿意承认它是凭势力存在或运作的。我们认为政府不过在提供道德的指引,和一个自我满足、自我表达的环境。我们承认独裁体制是靠威势运作,那种制度是错误的。但我们认为自己的国家不一样,至少我们希望它与那些独裁国家不同。
其实不然!或许我们的国家比较“仁慈、温和”,但它的铁拳隐藏在丝绒手套里。它也是依据着势力,原因很简单:每一个政府都建立在威势这个基础上。政府若没有势力,就根本无法运作。
举例来说,美国有一套所谓的“自愿”报税制度。你每年四月填税表的时候,会看到表格最上方有一段文字说,这是世界上一个相当独特的国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会“自愿”报税,“自愿”付出天文数字的税款,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自愿”申报!多么美好啊!当然,这不是事实。如果你拒绝缴所得税,就会被处以罚款,还要加上所欠税款的利息。如果你仍然拒绝缴交,就会遭到拘捕,你的产业会遭查封,以抵付欠税。
缴税根本不是一件自愿的事。这是必须尽的义务,其证据是,政府会使用势力强制达成征税的目的。
让我举另一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商人,你的生意受到政府各种繁复法律的规范。你有成堆的法规待遵守,各式各样的表格待填。于是你决定今年不填任何表格。结果呢?政府会勒令你停业,甚至捉你下监。
我将在本讲中探讨神所赐的这种势力,是在什么样的领域中运作。但我这样做之前,先要提出一点:执行法律的权力是神赐给政府,而不是给教会的。耶稣在彼拉多面前受审时,他知道彼拉多有权管辖他,包括将他处死的权柄。但耶稣并未替自己或门徒向神要求这种权柄。别人问到他的国度时,他回答说他的国度是真理的国度:“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18:37)。
每一次教会企图掠夺政府的权势时,教会就陷入麻烦。中古时代的教会曾企图这样做,在那之前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曾宣告基督教为国教,结果给教会带来不少灾难。教会领袖变得嗜权若渴,宗教真正的精神已化为乌有,腐败的情形与日俱增。
宗教领袖经常成为昏庸的统治者,因为世俗的权力腐蚀他们的程度远比腐蚀世俗的领袖为甚。因此神把佩剑的权力赋予凯撒,而不是教会;那种权力不能用在基督的事工上,只有凯撒拥有杀头的权力。
社会秩序
我们说到剑的权力已经交给政府,这并不表示政府可以任意使用它,也不表示政府可以运用这权力来做只有教会才能做的事,就是宣讲福音和真理。让我们来一一探讨。
1. 虽然政府的权力是神所赐的,但不可予以滥用。譬如说政府不能使用神所赐的权力去滥杀百姓。它也没有权力去为虎作伥。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说得很清楚,他重复提到行善的人和作恶的人,以及政府有权惩恶扬善。
那么该如何使用剑的威力呢?第一,政府有权力保护其公民免受境外仇敌和内部恶人的侵害。它有权宣战,包括运用一切必要的资源,例如征召百姓入伍,征收战争税,重新调整国家经济以适应战时需要。这些是立法权,但只能用在防卫需要上。例如单为作战而定的经济规章,就不能沿用到战后的承平时代。
政府也有权保护其公民免受内部恶人的伤害。这是说政府有责任提供和维持社会秩序。圣经作者似乎对这一点特别关切,或许是因他们比我们大多数人更体会到无政府状态的可怕。在那种情形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因此即使一个不良的政府也总比群龙无首要强得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为统治者代祷,包括邪恶的君王。保罗吩咐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提前2:1-2)。社会秩序本身是好的,特别是对基督徒,因为这能提供我们传播福音的大好时机。
教会可以用这种正确的角色来提醒当权者,鼓舞他们励精图治。加尔文说:“在上掌权的或许能从这里学到他们的呼召之性质。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治理,而是为了公众的好处。他们的权力也不是漫无限制的,必须限制在为百姓谋取利益的范围内。”
神赐给政府的权力,可以运用在第二个领域上,就是建立、运用、维持正义——亦即惩恶扬善。这是保罗在这几节中主要的用意:“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此处包括两件事,每一件都极其重要。第一,分辨善恶的观念攸关重大。保罗说政府有权惩罚恶人,他假定了一点:不仅个别公民必须遵守道德标准,整个国家也必须遵守。换句话说,政府应该奖励行善,惩罚作恶,但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知道善是什么,因此必须先有一个主观的道德标准存在,不论这标准是由政府自己发现的,还是来自它处。
这在今天尤其必要,因为美国律法在这方面曾经历过一次重大改革。约翰·怀特黑德(John W. Whitehead)针对此写了一本书,书名是《美国二次革命》。所谓二次革命,就是美国目前惯以富弹性、可以由法律学者决定的社会法律,来取代主观而不改变的法律。
让我加以解释。1907年,最高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第一次正式表达他从社会学角度对法律的了解,他说:“宪法完全依照最高法官的阐释而定。”他的意思是,法官是不受绝对法律限制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法律中找到自己所要的,甚至可以更改法律。因此你无法在最高法院的决定之外上诉,即使它与宪法或从前的法律相抵触。
然而最初拟定宪法的人,其见解却大不相同。他们认为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的国家是受制于法律,而非受制于人,或最高法院。这种观念来自苏格兰长老会的塞缪尔·拉瑟福德(Samuel Rutherford),和他那本不朽的著作Lex Rex,意思是“法律即君王”,以及英国法律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他将此观念溶进英国一般法律;另外还有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他是唯一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字的牧师,他也将这种观念注入了美国宪法。
让我附带一笔:这完全是因为殖民地(美国新大陆)的居民相信绝对的法律,即使法官也必须对其负责,所以他们认为反抗英国是合理之举。因为当时的乔治王违反了他们“生活和自由”的权利,这权利是“自然律和创造自然的神”所赋予他们的,所以他们决心反叛英国。
此处我要强调的重点是,国家秉公行事的能力,完全取决于绝对的法律,这也是基督徒看待政府权柄的唯一方式。若离开这一点,每一样事物都会变成相对的,早晚会破坏人人平等的可能性,而法官可以随兴之所至来判断人民。
2. 政府无法用权力来改造恶人。政府被赋予剑的势力,只是为了保护百姓和惩罚恶人。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政府有从神来的责任去刑罚恶人或恶劣的行为,但它没有权柄——其实也无能为力——去实际改变或更新作恶的人。
C. S.路易斯的文章“人道主义的惩罚原理”对此有极精辟的洞见。他在这篇文章里,将旧有报应式的制裁(一个人做了恶事,就依据其所行的恶受惩罚),和人道主义的观念(一个人受制裁是为了使他改过),彼此做一个对照。
旧有的观念是根据“罪有应得”的原则,一个杀人犯被判的徒刑当然远重于一个扒手,因为前者所犯的罪较大,理当受较严厉的惩罚。人道主义根据的观念则是:如何设法来帮助罪犯,使其改过自新。
当然,我们的制度是兼顾二者。判定刑期的长短固然根据罪行的轻重,但量刑之后,我们也参考犯人在狱中的表现,以及他是否有心理疾病,疾病是否已经痊愈等因素,酌情缩短刑期。至于第二种观念,可以表达在我们称监狱为“感化院”的事实上。犯人有机会在那里得到感化,或者改造,重新做人。
C. S.路易斯辩称,虽然人道主义的观点看起来满怀同情,也具启发性(它只谋求犯人的福利),但实际上这是很残忍的,原因如下:
第一,它把决定惩罚的性质和刑期长短之权从法官手中拿走,放在心理专家的手里。法官判刑时根据的是一个客观的司法制度,心理专家则是依据犯人何时能被感化来考虑。
第二,它贬低了所牵涉到的人。罪犯不再是一个有道德责任、能够犯错,也能够为所犯过错付代价的成年人。他被贬到了一个任由专家鉴定的对象;在达到专家定义中所谓的“痊愈”地步之前,他不过是一个“案例”。苏联政府对付政治犯的方式就是一例。
这带来第三个理由。C. S.路易斯写道:“如果犯罪和疾病被视为同一件事,那么专家所称为‘病态’的任何一种心理状况,都能被视为罪行对付,都必须强制接受治疗。”对此,即使别人不在乎,至少基督徒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基督教从未广受欢迎,任何一个有威力的政府,都可以打着医治我们那些“反社会性”或“仇视人类”的信仰或行动之旗号,将我们关起来,直到我们的理念被“治愈”为止。
当然,罗马书第13章的意思是,使人民得医治根本不是政府的事,神只是使用政府来惩恶扬善。因此政府必须有一个是非标准,并且公正无私地维护这标准。这是政府长远的职责。
神的子民在哪里?
关于政府如何使用权力,我还要提出最后两点。
1. 政府无法增进道德。政府只能惩罚,却不能增进公民的道德。当然这句话里最重要的一个词是“增进”。我不是说政府不必关心道德问题。相反的,政府绝对不可忽视道德,因为道德是法律唯一的真正基础。
举例来说,如果政府通过一条禁止偷窃的法律,并且运用剑的权力去严加执行,这条法律和附带对违犯者的惩罚,其唯一有效的基础就是“偷窃是错误的”。或者换一种方式说,神给人拥有私产的权利。如果偷窃不是什么坏事,那么政府对偷窃的反对和惩罚行动就是独裁,是不公平地侵犯了人的自由。如果偷窃是错误的,那么政府的行动就正确无误。法律也是如此。法律唯一有效的基础就是现已存在的道德。
再举一个例子。例如死刑,政府有权夺去一个杀人犯的生命,其唯一的根据是创世记9:6,那里说到杀人者偿命,因为他杀了一个“神照自己的形像造的”人。这表示他的行动违反了神的律法,得罪了神。
然而对道德的关切并不表示政府能够增进公民的道德,因为政府做不到。它能禁止,惩罚。它能强制执行禁令,这也许多少能限制一些恶行。但它不能改变所涉及的人。
禁酒令即是一例。美国政府曾禁止销售酒精饮料。虽然交易行为减少了一些,但酒的销售额却直线上升;一旦禁酒令撤消,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2. 道德来自启示的宗教。既然政府不能增进公民的道德,那么道德一定有另一个来源和发展的方式。那个来源是什么?道德是从哪里来的?只有一个答案。它来自启示的宗教,而且必须透过那些认识神、诚心讨神喜悦的公民,将其引入国家生活里。
因此虔诚的百姓乃是国家最大的资产,只有他们能将国家导向公平和真正的公义之途。今天我们的需要不是制定更多法律。我们若没有讲道德的公民,即使法律也可能被用在不道德的事上。它们可以被用来逃避债务、逃脱监狱刑期、欺诈无辜、压迫穷人,以及各种作奸犯科的事。我们需要的是一群知道并且愿意靠着顺服神的律法而活的人。
我想起历代志下7:14。那段伟大的旧约经文提供了一个使国家得医治的方式;那并不是推翻旧的君王,另外选出一个较英明的领袖。它甚至未建议制定一套更理想的法律。它乃是呼吁神的百姓借着悔改而更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本文选自《生命宝训讲道注释系列——罗马书》
作者:博爱思(James Montgomery Boice)